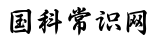鹿邑食光錄八味千年里的天地人和
作者:佚名|分類:生活雜談|瀏覽:83|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25-08-14
天光未明時(shí),青石板路上已然沸騰起人間煙火。我踩著露水往老街深處去,忽被一縷溫?zé)岬亩瓜憬O住了腳步——這熟悉的氣息,是鹿邑人用百年時(shí)光熬煮的晨光序曲。
木桶掀開的剎那,乳白的霧氣裹挾著豆香撲面而來(lái),恍如看見渦河在晨曦中舒展腰肢。黃豆與小米在石磨里纏綿整夜,濾出的漿汁在柴火灶上跳著圓舞曲,直到熬出這碗“白玉漿”。撒幾粒腌黃豆,配兩根現(xiàn)炸油條,看外鄉(xiāng)人學(xué)我用筷子尖挑著油條蘸奶湯,忽然懂得老輩人說(shuō)的“碗底乾坤”——這傳承百年的媽糊,最是藏著鹿邑人骨子里的中庸之道。
正午蟬鳴最盛時(shí),巷口那間無(wú)招牌的棚屋藏著驚喜。山芋粉在井水里醒成顫巍巍的“娃娃魚”,老板娘手腕輕抖,晶瑩的涼粉便滑進(jìn)滾燙的雞湯。荊芥葉與辣椒油在碗中畫出陰陽(yáng)太極,哧溜一口,冰涼與火辣在舌尖纏綿,暑氣化作額角細(xì)密的汗珠,痛快得讓人想起老子說(shuō)的“道法自然”。

孔集老街的百年老灶前,第七代傳人老張正往陶罐里添著陳年老湯。這鍋始于嘉靖年間的鹵水,見證過(guò)多少代貢雞的涅槃?“要選養(yǎng)足百日的蛋雞,抹蜜油炸再文火慢煨。”琥珀色的油光里浮著完整雞形,筷子輕撥卻骨肉分離。學(xué)著老輩人撕塊雞肉夾進(jìn)火燒,外酥里嫩的層次間,忽然嘗到時(shí)光沉淀的醇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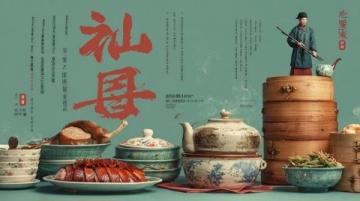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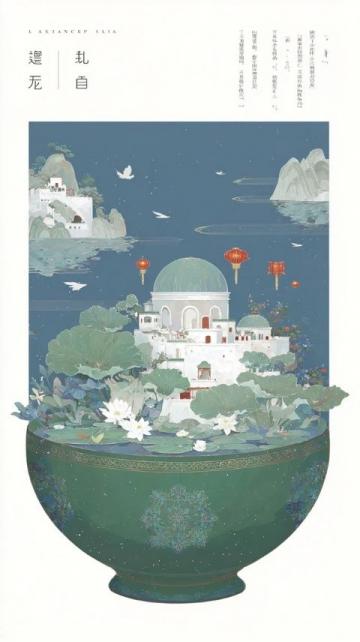
觀堂作坊的老師傅手腕一翻,剛搟好的糖片便輕盈飛起。這傳承自南唐的絕活,講究“薄如蟬翼,落地即碎”。芝麻粒在夕陽(yáng)下跳著華爾茲,咬下的瞬間,酥脆聲在齒間炸開,甜香裹著芝麻香直沖天靈蓋。恍惚看見千年前的匠人也是這樣守著炭火,把四季輪回?fù){成薄如紙片的思念。
冬至夜的試量鎮(zhèn),空氣里飄著古老的約定。夾起顫巍巍的肉片蘸蒜泥,辛辣與醇厚在舌尖綻放,忽然懂得“狗肉滾三滾,神仙站不穩(wěn)”的俗諺——這暖身更暖心的滋味,原是刻進(jìn)中原人基因里的冬日情書。

五更天的邱集窯洞,上演著面團(tuán)變形記。反復(fù)摔打的面團(tuán)裹著五香粉,在案板上開出層層疊疊的花。當(dāng)燒餅貼進(jìn)炭火壁爐,我聞到了麥香與火焰的私語(yǔ)。十分鐘后,捧著燙手的燒餅咬開酥脆外殼,熱氣裹著椒鹽香直沖鼻腔,突然明白老師傅說(shuō)的“好燒餅要會(huì)呼吸”——那層層疊疊的氣孔,不正是土地對(duì)麥浪的深情告白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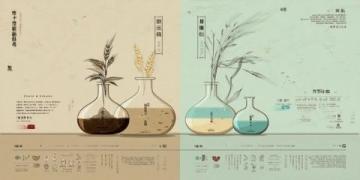
辛集老街當(dāng)中秋臨近,作坊里又會(huì)飄出玫瑰與核桃的甜香——辛集月餅的酥皮要搟足十八層,包進(jìn)青紅絲與冰糖的月光。咬開月餅的剎那,月餅要甜得能流蜜,才是辛集人的待客之道。“

暮色染紅宋河時(shí),我總愛坐在老酒坊的門檻上。看晶瑩的酒液從紫砂壺嘴傾瀉而下,空氣中綻開高粱與曲香的二重奏。至今仍是老酒客們心頭的白月光。舉杯對(duì)月的剎那,忽然懂得老子說(shuō)的“道法自然”——這杯中日月,原是比道德經(jīng)更醉人的生存哲學(xué)。
離鄉(xiāng)那日,我把媽糊碗底的最后一滴舔凈。當(dāng)現(xiàn)代美食沖擊著每個(gè)城市的味蕾,鹿邑人依然守著老灶臺(tái),用千年時(shí)光熬煮著最樸素的幸福。這或許就是老子故里最動(dòng)人的生存智慧:萬(wàn)物歸真,味從本心。


(責(zé)任編輯:佚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