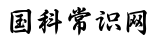盛夏里的時光對話:瓷城日記之旅
作者:佚名|分類:生活雜談|瀏覽:89|發布時間:2025-05-15
《瓷城日記:盛夏里的時光對話》
【壹·陶溪川的秘密】
2018年的夏日傍晚,我和老岳在陶溪川夜市的人流中走散。那時夕陽的余暉將紅磚建筑鍍上了青銅般的光澤,大學生攤主們手持著發光的陶瓷作品,仿佛握住了來自遙遠星球的碎片。我在一個拐角處偶遇一只能夠變色的茶杯——注入熱水時,杯子內壁浮現出了《陶冶圖》中的赤膊匠人圖案。小唐告訴我這是用熱敏釉料復制故宮藏品的結果,但我總覺得這更像是乾隆年間某個工匠未完成的夢想。
老岳發來的定位顯示他正蹲在廢舊的老廠路拍攝延時攝影。拆遷進行到一半的車間里,明清時代的瓷片和90年代的搪瓷碎片共存于一處,晚霞穿透屋頂的裂縫,在地面上投下了青花纏枝圖案的光影。“這難道不像是時間的窯變嗎?”他指著縫隙中探出頭來的蕨類植物說。我們的身影被拉長成了兩把修坯刀,切割開凝固的記憶。

【貳·泥土的啟示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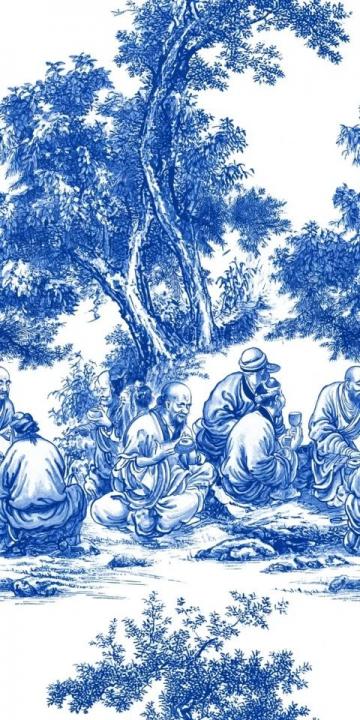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早晨,在雕塑瓷廠內,七十歲的李師傅教我們揉泥。他說景德鎮的泥土需要“醒”足四十九天,如同老面發酵般等待蘇醒的過程。當我第三次將拇指嵌入泥團時,他突然回憶起1995年國營廠改制那天:三千名工人聚集在最后一座倒焰窯前,把未燒成的半釉陶坯砸得粉碎。“那聲音比雷雨還要沉悶,碎瓷片鋪滿了三條昌江。”
老岳的手工茶杯在拉坯機上失控旋轉,最終變成了一件歪斜的抽象藝術品。李師傅用三根竹簽為它雕刻出冰裂紋:“殘缺正是陶瓷的靈魂。”我們捧著各自的作品前往電窯時,暴雨突然降臨,青石板縫隙中涌出了混雜著高嶺土顆粒的小溪,整條街道仿佛正在重新回歸史前的河床。
【叁·夜宴考】
在西虹路的夜市大排檔里,油燜小龍蝦與青花瓷盤形成了一種奇特對話。老板老周用裂紋釉碗盛著堿水粑,他說這是使用古法釉水修復過的:“破損的瓷器和完好無損的瓷器,在我這里都能繼續發揮作用。”他指著墻上的泛黃獎狀——1987年國營瓷廠先進工作者的照片中,二十歲的他曾為隧道窯添柴。
我們循著酒香走進巷尾的一家地下酒吧,調酒師用永樂甜白釉高足杯裝特飲。《陶歌》的投影突然卡頓,像素化的“匠從八方來”字樣與窗外的美團騎手身影重疊。半醉時聽到駐唱樂隊把《青花瓷》改編成了雷鬼版曲目,老岳說:“這座城市不就像是正在經歷窯變的巨大瓷器嗎?”

【肆·碎瓷紀】
在御窯博物館的最后一日,暴雨洗亮了玻璃幕墻,映襯出明代葫蘆窯遺址。講解員演示AR眼鏡時,成化年間的把樁師傅與我們的身影在虛擬空間里重疊。觸摸龍珠閣出土的宣德青花大罐時,修復裂痕中的金繕膠微微發熱,仿佛觸及到了某個匠人未涼的身體溫度。
歸途前我淘得一套九十年代國營廠瑕疵品咖啡杯。五年后當我用其中一只飲茶,發現杯底竟然出現了當年未曾注意到的窯粘痕跡——那是景德鎮留給我的隱秘印記,提醒著每一份完美背后都藏著時間與火候的秘密。
(責任編輯:佚名)